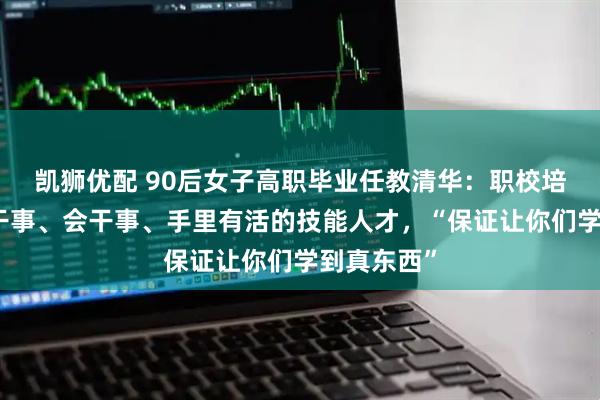香港东亚书局1973年出版
香港东亚书局1973年出版
知道郁达夫之名,甚早;读到郁达夫之文,却很晚。个中缘由,也很简单:我的少年时期,正赶上“十年书荒”。很早知晓郁达夫,皆因鲁迅先生那首名诗《自嘲》,诗中那副“横眉冷对千夫指,俯首甘为孺子牛”的对联,在那十年间依旧流行。就在该诗手书的题跋中,鲁迅写明是“达夫赏饭,闲人打油”。在注释中讲到这个“赏饭”者牛360配资,就是郁达夫。可是,彼时郁达夫的书尚属“毒草”,封禁很严,一般人是看不到的,更何况像我这样的孩子。
开始读到郁达夫的书,已到上世纪70年代末。当时解禁了不少书,我在一本现代文学名著的选本中,第一次读到郁达夫的小说《沉沦》。后又在另一个选本中,读到他的《春风沉醉的晚上》和《迟桂花》。只觉得他的小说中有一种忧郁之美,迥异于当时那些更有名的作家们。再到后来,读到他的散文,尤其是读到名篇《钓台的春昼》,才像发现新大陆一般,狂热地喜欢上了他的散文。直到现在,我已年过花甲,却依然初心不改。喜欢郁达夫有诸多理由,其中一条就是,他很喜欢在散文中插入自己的诗词。譬如在《钓台的春昼》里,他便引述过自己写的几句“歪诗”,其中“曾因酒醉鞭名马,生怕情多累美人”一句,尤为令人过目难忘。当时就想,一个新文学名家,却喜欢在文中点缀自己的旧诗,这种写法恐怕惟郁氏独有吧?这种白话文中夹带旧诗的“郁氏笔法”,我后来也时常在写散文时采用。
喜欢一个作家,自然就会留意搜罗他的著作。无论全集还是选本,见到了总不免心动。近期翻出这本买了却一直未读的《烟影》,暑天燥热,正好拿来闲读度暑。
这是从香港旧书店淘来的一本旧书,香港东亚书局1973年出版,应该是1997年我赴港采写《回归的脚步》系列报道时,抽空从旺角一带的某家小店里淘来的。当时实在太忙,没顾上细读,将书塞进书架里就淡忘了。退休后从深圳回到北京,大量的书籍都留在了深圳——包括早年购藏的花城版12卷本的《郁达夫文集》,却不知为何,把这本不起眼的小书带回北方,这大概算是一种“书缘”吧。如今有了空闲,终于可以静下心来,阅读这本颠簸辗转大半个中国的小书了。
《烟影》一书无前言无后记,很可能是香港书商为卖钱私攒的出版物。但是,你却不能说这个编者没有水准。只需把书中的篇目与大陆出版的诸多郁氏选本对照一下,就会发现他们还是很有眼光的。全书分为上下两辑,上编为小说,下编为散文。《烟影》的书名取自上编中的一篇小说。这篇小说在内地的选本中很少见到牛360配资,写的是一个失业的年轻文人思乡心切,却囊空如洗,偶遇一位旧友,互问近况之后,旧友执意送给他一个银质烟盒。他说自己得了肺病,早就戒烟了。但朋友一定让他收下,汽车开动时才甩回一句话:“烟盒的夹层里,还有几张票子在那里,请你先用……”他有了这几张票子,立即跑去车站购票回家了。至于回到家后的琐细情节,就无需赘述了。单凭这个细节,就足以令人印象深刻。
《烟影》一书把小说与散文“合璧”的编辑体例,对我而言还有一个好处,就是把《采石矶》和《关于黄仲则》这两篇文章,兼收于一书之中——这样一来,小说原作和创作这篇小说的作者自述,于一册之内即可通览了。《采石矶》是郁达夫历史小说中的名作,流传甚广。其对清代诗人黄仲则的形象刻画,带有浓重的悲凉孤寂的色调。这种淡灰色的调子与其描写当代文人的作品,比如《沉沦》《烟影》和《银灰色的死》可谓异曲而同调。而小说中黄仲则怒斥彼时文场酸腐、官场堕落的段落,着实是看着解气,不禁为之击节——“他们今日讲诗学,明日弄训诂,再过几天,又要来谈治国平天下,九九归原,他们的目的,总不外乎一个翰林学士的头衔。我劝他们还是去参注酷吏传的好,将来束带立于朝,由礼部而吏部,或领理藩院,或弄个内阁大学士的时候,倒好照样去做。”他的好友洪稚存闻言,立即劝阻他:“你又要发痴了,你不怕旁人说你在妒忌人家的大名吗?”黄答曰:“即使我在妒忌人家的大名,我的心地,却比他们的大言欺世、排斥异己,光明得多哩!我究竟不在陷害人家,不在卑污苟贱的迎合世人。”读到这里,我每每猜测:这些激愤之言,又何尝不是作者对当世乱象的不平之音呢!
读罢小说,再翻到后辑去读他的《关于黄仲则》,两相对照,顿时文脉贯通——原来对于黄仲则,郁达夫自少年时期便“一往情深”。他同情其身世,悲悯其早亡,更钟爱其诗文。在这篇文章中,他写到了十多年前创作《采石矶》的初衷:“把那全集(指黄仲则《两当轩集》)细读了两遍之后,觉得感动得我最深的,于许多啼饥号寒的诗句之外,还有他的那种落落寡合的态度,和他那一生潦倒后的短命的死。……以‘母老家贫子幼’之身,又加上了‘狂傲少谐’‘上视不顾’之习,终至于为养亲糊口之故,想谋一县丞而未得,却早为债家所迫,抱痛而逾太行。正值三十几岁的壮年,不得不客死在黄河东岸,山西的运城。”郁达夫说,当时读了洪稚存所写的黄仲则行状之后,“心里头真感到了异样的辛酸,所以在那时候,曾以黄仲则为主人公,而写过一篇《采石矶》的小说。翻开这小说的刊行日子来看看,是一九二二的十一月,计算起来,去现在,已经将满十年了。”
翻开这篇《关于黄仲则》的文末,注明是写于1932年6月。由此,可知郁达夫是很在意时间概念的。他绝对不会预料到,自己会在1945年9月17日被凶残的日军杀害于苏门答腊丛林中——而当时的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,驻留当地的日军恐是发现了他的抗日迹象,竟疾速对他下了毒手。他是死于抗战胜利之际啊!
郁达夫死后被追认为抗日殉国的革命烈士。每每想到他被害的时间节点,不禁喟然长叹:去现在,已整整八十年了!
(作者为深圳报业集团原副总编辑)
更多热点速报、权威资讯、深度分析尽在北京日报App
作者:侯军
科元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